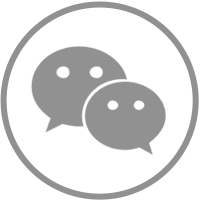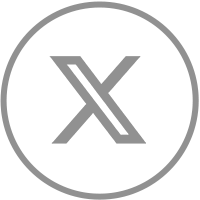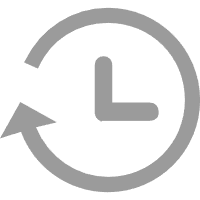(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小說家王安憶說:莫言有一種能力,就是將現實生活轉化為非現實生活,沒有比他小說裏的現實生活更不現實的了。莫言,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公認的中國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大師。
不知是否偶然,莫言「將現實生活轉化為非現實生活」的這種魔幻能力,多次出現在去年11月下旬為劇作《鱷魚》在香港上演而至的數天密集行程中:在他下榻的港島香格里拉酒店55樓套房,一眾媒體拍攝小組正在外間悄聲調試設備。兩面開闊的落地大窗正對維港,窗外碧空澄澈,九龍半島的高樓天際線和遠方的獅子山迤邐起伏。當莫言先生從臥室低調走出時,一台起降機剛好從窗外降下,兩名外牆清洗工人突兀出現。莫言和他們就這樣靜靜隔窗對視而立,幾厘米玻璃幕牆,隔開了兩個世界。
而在前一天夜晚,維港上空還演出了一場大型無人機秀:在兩岸璀璨燈火輝映下,一條巨鱷排空而來,四足騰空爬動,大嘴還一張一合,最後幻化為一條祥瑞巨龍。傍晚剛從北京飛至的莫言先生則在現場接受媒體群訪。莫言劇作《鱷魚》即將在港上演的宣傳預告,就這樣奇幻顯現。
一位憑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雄奇的寫作才華和澎湃不已的表達激情,以一人之能,在40年時間長河中,一路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招兵買馬、行軍布陣、大開大合,創造了中國文學中瑰麗迷人的「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寫作時一個接一個的靈感奇想「像狗一樣在身後瘋狂追趕」的小說國王,在57歲獲得諾獎、人生漸入後半場之際,以一種前半生無法想像的鬆弛方式,放慢了開疆拓土的步伐。
應該說,作家莫言的出現,是造物主創造生命的玄奧處。他長期生活在中國農村社會的最底層,小學畢業就回村從事農業勞動,從1950年代自膠東半島壓抑貧瘠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有吃煤塊的飢餓記憶,與自然為伍,和天地對話,飢渴閱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21歲抓住入伍服役機會,怎麼就奇跡般改變了人生命運?聽故事的人逐漸變成寫故事的人,帶着對那塊鄉村土地的記憶、想像和書寫,越走越遠,一個人穿越了千山萬水,從亞歐大陸最東岸中國山東的一個小村莊,走到最西北的瑞典斯德哥爾摩領獎台一隅。上帝看似隨意播下的一顆生命種子,居然以一支魔幻之筆,創造出讓讀者心馳神蕩、五內搖撼的新大陸。這也是文字之外莫言自己真實的魔幻戲劇人生。
莫言在各種公開演講和媒體受訪時(順便說一句,他的全世界各地演講集已出版了洋洋灑灑三大本),反覆掏心窩子地坦誠創作初衷:飢餓和孤獨是創作的源泉。「長期的飢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我最初的寫作動機,既不高尚也不嚴肅;我曾說過,我之所以要寫作,是因為我想過上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幸福生活——對不起,又與飢餓和食物有關。我也曾說過,之所以寫作,是想掙點稿費,買一雙皮鞋,買一塊手錶,回村去吸引姑娘們的目光——對不起,依然很庸俗,很功利。但隨着時光的推移,我已經有條件實現每天三頓吃餃子的夢想,我已經不願穿皮鞋不願戴手錶,但我的寫作一直在繼續。這不得不使我認真地審視:到底什麼是我真正的寫作目的?」
莫言說:「回顧幾十年來的寫作經歷,觀照了我目前的寫作和心理狀況,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正的寫作動機,是因為我心裏有話要說,是想用小說的方式,表達我內心深處對社會對人生的真實想法。」對寫作藝術的迷戀和迷宮探險般的實驗創新,是支撐莫言不斷寫下去的動力。
天才如莫言,當然也有自己的文學師承脈絡。由蒲松齡開啟的志怪小說、地方戲曲和民間文學滋養,文以載道、針砭現實、為民發聲的中國傳統主流文藝觀念的思潮浸潤,再加上「兩座灼人的高爐」作家福克納、馬爾克斯和適時出現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影響,以及作家、思想家魯迅的冷峻、遼闊和悲憫,對故鄉生活的親切記憶,都是促成莫言文學成就一路綻放的隱秘精神因緣。
一個自承「在飢餓、孤獨和恐懼中長大的孩子」,「從小就不乏說真話的勇氣,甚至可以說,說真話是我的天性,但我的勇氣和天性在我少年時期遭到挫折和壓抑。那是一個一句話說不好就可能帶來災難的時代,我母親對我喜歡說話的天性憂心忡忡,她一再告誡我要少說話。」成年後居然以「莫言」為名,多少有些自嘲意味。不過,「更換了名字,但並沒有改掉天性,只要我一拿起筆,話語就如決堤的江河滔滔而出。我想,少年時期我少說了的話,都在後來的寫作中,變本加厲地得到了補償。」莫言容納了歷史想像和現實描摹、以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奇兵突出、既天馬行空狂放奔湧同時又怒濤入海金石俱下的文本創作,飽含了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及背後文化體制根源的同情與理解、諷刺與嘲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其「我爺爺」、「我奶奶」(《紅高粱家族》)、上官金童(《豐乳肥臀》)、劊子手(《檀香刑》)等包含對中國人生命寄望和國民性格思考的人物塑造,都是中國文學創作中的異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第一次來香港是在1990年,35年後對香港的觀察和看法怎樣?香港文化是否對您有過影響?記得2007年的香港書展上,您評論香港是「文化的綠洲」。
莫言:1990年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我來做訪問學者,待了一個月。主要是中文大學的翻譯研究中心把我的十幾篇短篇小說翻譯成英文,要我幫助解決翻譯當中遇到的問題,一些方言土語、民間風俗之類。當時來香港手續極其難辦,那時我還在部隊服役,所以要經過很高機構的批准,過了8個月才完成。來了香港後第一次跟着一個中文大學老師逛超市,真是眼花繚亂,什麼商品都有,多得過剩的感覺。(商場)裏面竟然能吃飯,能看電影,什麼都可以。當然這樣巨大的商場,現在北京上海也到處都是了。當時是我第一次來香港,後來每隔一兩年都來,也有時一年都來好幾次了。有時去台灣,要從香港路過,那會兒去台灣要在香港中轉的。
這種商品和文化產品供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我童年完全不同。我小時候能讀到的書很少,村子裏小學老師的書、左鄰右舍的書,也就那麼幾十本,看一遍以後就感覺到全看完了。戲劇也是這樣,那時縣茂腔劇團一年可能頂多下來一次,那種下鄉巡迴演出。我當時還是孩子,張家村看了,李家村看,一路都跟着,一直跟到很遠的村子,我們才不去了。所以我那時受到的文化熏陶,觀看的舞台戲和電影,都極其有限。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和文化環境裏成長起來,對比香港,我當然感覺到這裏非常繁榮了。
我看過一些香港早期的電影,像《三笑》《巴士奇遇結良緣》等。還有很多戲劇電影,都是內地文化跟香港電影行業的結合,唱的可能是江南的採茶調、廣東的粵劇、浙江的越劇,大量電影在上世紀60、70、80年代製作出來,其中也包括以成龍為代表的警察電影等。談香港就離不開武俠小說,天下哪裏有華人,哪裏就在讀金庸;香港那麼多電影公司,也受益於武俠小說創作的大繁榮,這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流行文化之外,香港還有嚴肅文學、現代派的寫法,有西西,後來的董啟章等,現在也還有大量文學作者。中國作家協會從去年開始非常密切地與港澳作者聯繫,一個幾十人的代表團去中國作協訪問,我也參加了兩次活動,很多年輕作者我還叫不出名字。也有很多內地學者和年輕作家在香港這邊讀書工作,比如葛亮,包括老一代的黃子平、許子東,當年在內地都是屈指可數的文學評論家。還有香港的商業文化,也都值得一說。所以從這些綜合角度來看,我覺得香港不是「文化的沙漠」,而是「文化的綠洲」。
香港文匯報記者:民間文學對您的滋養很深,您文學素養的早期來源,就有民間戲曲、蒲松齡志怪小說等。剛才您也談到了對金庸、香港流行文化等的看法。不過有人或許未必同意,比如王朔就曾說它們屬於「四大俗」(流行音樂四大天王、瓊瑤言情劇、成龍電影、金庸武俠小說),您怎麼看?
莫言:我和王朔是特別好的朋友,我很尊重他,我喜歡他這個人的坦蕩直率。王朔有一種頑童的性格,有時候可能情緒上來了,誰惹他不高興了,就先罵你一通再說,過後再來向你道歉。這都是沒問題的。王朔這個人非常善良,我跟他一塊去意大利,當時我、余華、蘇童,我們1990年代末一塊去意大利,四個人,每兩個人一個房間,有時候一個房間裏一個大雙人床、一個小孩床,王朔永遠讓我睡大床。有的時候他還睡地板。很多細節可以顯示出他的寶貴品質。
他對金庸的評價我當然不同意了,但他可以保留他的觀點,他也是自己切入的一個角度,能夠自圓其說就行。文學批評是這樣,你只要能自圓其說,是一家之言,就可以存在。當然,如果自己都圓不了自己的說法,那就不能成立。從這個角度來講,王朔酷評金庸,我認為也是可以的。我高評金庸,他也不能反對我。當然我們兩個人也沒因這個坐在一塊辯論一下,你為什麼說金庸不好?你為什麼說金庸這麼好?不至於。大家都明白這是文學,完全可以並存對立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剛才談到了香港的嚴肅文學創作,您對西西的小說評價很高,說她是「香港第一個魔幻現實主義作家」。您願意談談您了解的香港其它文本寫作嗎?比如說詩歌、專欄寫作。
莫言:我對台灣的老一代詩人像瘂弦、管管、大陸流行特別廣的余光中,包括商禽他們的作品了解多一些,我感覺水平很高。香港詩人的作品我真的讀得比較少(記者補充:香港詩人中有也斯等),我讀他散文比較多。
香港是報紙非常發達的地方,報紙專欄是一種文化現象。內地的很多報紙也都有副刊,像《羊城晚報》的「花地」,就培養了大量作者。《天津日報》的「文藝周刊」,孫犁先生主持的時候,就是一批白洋淀派作家的陣地。當年《北京晚報》有「三家村札記」,作者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文章有知識性和趣味性,對歷史有獨特見解,他們寫的不是小文章。香港有這麼多報紙,肯定要靠副刊來吸引文學愛好者,培養年輕作者。包括金庸先生他們的武俠小說,也基本都是在報紙上連載。我覺得第一陣地很重要,第二也鍛煉出了一大批作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1980年代深度參與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對當時香港的電影創作也比較了解。香港有非常世俗熱鬧、反映市井現實生活的電影,比如周星馳的,也有包括王家衛那種有濃郁作者風格的精英氣質電影,您怎麼看待香港電影當時呈現的多元現象?
莫言:我覺得電影的創作風格跟小說的風格是一樣的,當某種電影風格到達了一種極高的高度、很難逾越後,別的導演、創作者就會另闢蹊徑。小說家也一樣,你能再寫出個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嗎?寫不過了,那就玩法國新小說、意識流,這樣才有立足之地。當然過兩年可能有人又回來寫巴爾扎克式的長篇小說,然後又走紅了。藝術沒有新舊之分,也沒有過時之說,它就是不斷地旋轉。跟時尚也有一定關聯:今年流行紅裙子,明年藍裙子,10年以後又是紅裙子。所以電影的風格應該多樣化,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如果只有一種模式,就離死亡很近了。只有多樣化的存在,百花齊放、各種風格、各取所好,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繁榮創作的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以小說成名,獲得巨大聲譽,獲諾獎後您曾說以後要致力於戲曲戲劇寫作。您的戲劇創作呈現出多種路向:一個是荊軻和項羽這樣放置於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下的人物塑造,姑且稱之為新歷史主義戲劇寫作吧;一個是包括香港公演的這齣《鱷魚》,還有2017年的《錦衣》,都仍然具有您小說創作中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在中國的戲劇創作領域,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地位崇高,被尊為人藝學派,但其核心仍然是現實主義戲劇,對此您怎麼看?
莫言:人藝是有自己的戲劇傳統的,以《茶館》為代表,後來有《狗兒爺涅槃》,最近十幾年有劉恒的《窩頭會館》等,這都是人藝話劇的代表作。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也出現了像高行健等創作的一批實驗話劇,包括奇人故事型的《鳥人》等,《鳥人》裏面也有一些超現實的情景。當然,人藝主打的肯定還是像《茶館》這樣的戲,長年常演,包括曹禺先生《雷雨》的這種風格。我覺得主要還是從莎士比亞那邊繼承過來的嚴肅戲劇傳統,這種體系主要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系,學蘇聯那一套戲劇理論,要讓演員跟角色混為一體,讓觀眾和演員都進入到情境裏去。台上台下、戲裏戲外都渾然一體,好像就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大家跟着哭、跟着笑、跟着樂。而不是布萊希特那種間離效果。當然後來很多劇也融進了各種體系的東西。有的戲就是要製造一種特別冷靜的思索空間,不讓你沉浸,你剛要沉進去,就給你拽出來。這些戲劇傳統各有各的長處,我覺得我都能接受。
我的第一部話劇就是《霸王別姬》,是寫給空軍話劇團的。後來他們出國演出的時候叫藍天話劇團,肖雄、吳京安這些演員,都因為演這個戲獲得了梅花獎。《我們的荊軻》是空軍話劇團接了這個戲,演了幾場後,話劇團解散了,劇本就扔在了那個地方。過了十幾年後,大概到了2011年,人藝當時的年輕導演任鳴把這部戲撿了過去,我又重新改了一下,這戲也成了任鳴的力作。
後來我獲獎(2012年諾獎)之後,人藝老院長張和平就約我寫新戲,直到十多年後、2022年我把《鱷魚》寫出來。張和平帶着任鳴、霍志靜來找我,他們一致認為,這個戲人藝一定要排,而且馬上要在第二年的春節就要推出來。但是很不幸,任鳴那個夏天突然去世了。馮遠征接任院長,他的藝術觀點跟兩個前院長不太一致,他留學德國的,學布萊希特。他認為《鱷魚》這個戲太長,我寫了53,000字,對一個劇本來講,如果要全部演完,差不多要4個小時。當然在俄羅斯的話,話劇《靜靜的頓河》演8個小時的也有,《戰爭與和平》演8個小時的也有,那是特殊情況了。他希望我能壓縮到3萬字左右,我覺得很為難。正好這個民營戲劇團央華戲劇感興趣,說:不改,我們可以演。而且三個半小時,中間沒有劇場休息。所以就給他們了。人藝是個偉大的戲劇群體,我也答應了再給他們寫戲。當時我把《鱷魚》拿走後,我給馮院長說我會寫一個適合你們演的戲,現在還沒寫完。
(來源:香港文匯報A14:名人薈 2026/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