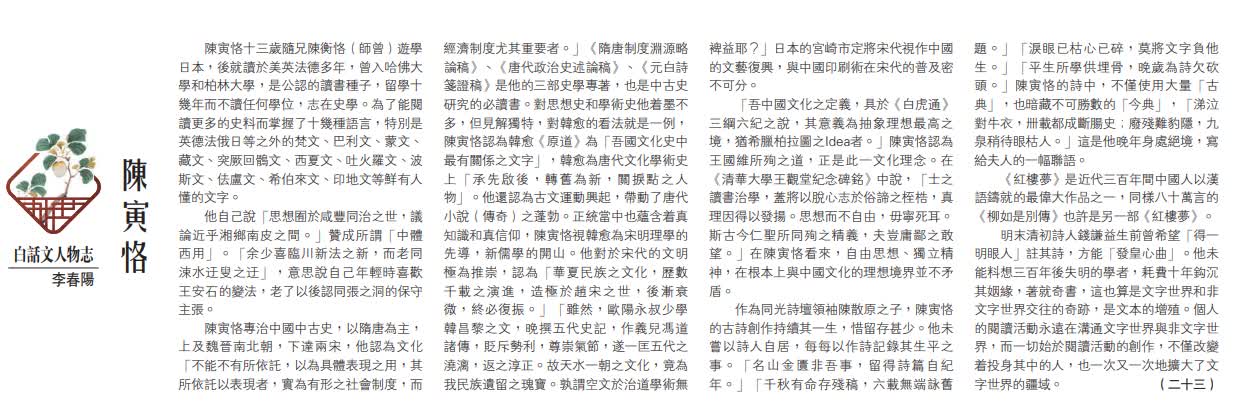
文/李春陽
陳寅恪十三歲隨兄陳衡恪(師曾)遊學日本,後就讀於美英法德多年,曾入哈佛大學和柏林大學,是公認的讀書種子,留學十幾年而不讀任何學位,志在史學。為了能閱讀更多的史料而掌握了十幾種語言,特別是英德法俄日等之外的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回鶻文、西夏文、吐火羅文、波斯文、佉盧文、希伯來文、印地文等鮮有人懂的文字。
他自己說「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贊成所謂「中體西用」。「餘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意思說自己年輕時喜歡王安石的變法,老了以後認同張之洞的保守主張。

陳寅恪專治中國中古史,以隋唐為主,上及魏晉南北朝,下達兩宋,他認為文化「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重要者。」《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是他的三部史學專著,也是中古史研究的必讀書。對思想史和學術史他着墨不多,但見解獨特,對韓愈的看法就是一例,陳寅恪認為韓愈《原道》為「吾國文化史中最有關係之文字」,韓愈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他還認為古文運動興起,帶動了唐代小說(傳奇)之蓬勃。正統當中也蘊含着真知識和真信仰,陳寅恪視韓愈為宋明理學的先導,新儒學的開山。他對於宋代的文明極為推崇,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日本的宮崎市定將宋代視作中國的文藝復興,與中國印刷術在宋代的普及密不可分。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之Idea者。」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所殉之道,正是此一文化理念。在《清華大學王觀堂紀念碑銘》中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在陳寅恪看來,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在根本上與中國文化的理想境界並不矛盾。
作為同光詩壇領袖陳散原之子,陳寅恪的古詩創作持續其一生,惜留存甚少。他未嘗以詩人自居,每每以作詩記錄其生平之事。「名山金匱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千秋有命存殘稿,六載無端詠舊題。」「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負他生。」「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陳寅恪的詩中,不僅使用大量「古典」,也暗藏不可勝數的「今典」,「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這是他晚年身處絕境,寫給夫人的一幅聯語。
《紅樓夢》是近代三百年間中國人以漢語鑄就的最偉大作品之一,同樣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也許是另一部《紅樓夢》。
明末清初詩人錢謙益生前曾希望「得一明眼人」註其詩,方能「發皇心曲」。他未能料想三百年後失明的學者,耗費十年鈎沉其姻緣,著就奇書,這也算是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交往的奇跡,是文本的增殖。個人的閱讀活動永遠在溝通文字世界與非文字世界,而一切始於閱讀活動的創作,不僅改變着投身其中的人,也一次又一次地擴大了文字世界的疆域。 (二十三)
相關推薦新聞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