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經緯/白日神遊\吳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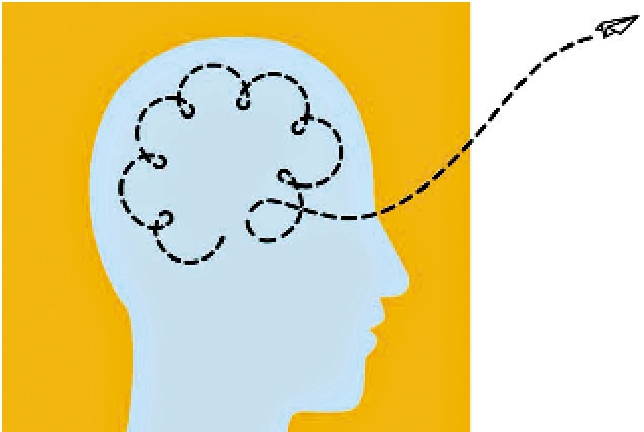
Celestial Seasonings是北美最大的茶葉公司,我曾多次造訪。它出品的各類茶葉,包裝紙盒設計得很漂亮,每一盒都印有一條名人名言。印象很深的一句是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Those who dream by day are cognizant of many things which escape those who dream only by night.」Dream by day,中文直譯「做白日夢」,但這個詞有貶義,比喻妄想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按照愛倫·坡的本意,最好譯為「白日神遊」。
開會時最宜神遊。眾人機智明辯,我就無需置喙。眼見唇唇齒齒嘈嘈切切錯錯雜雜喋喋不休,我的大腦就漸漸進入隱約迷離的狀態,起初像一鍋魚生粥,黏稠而半透明,後來慢慢稀釋淡去,只餘一片空白,是謂「神遊」。
聽課時也可神遊。大學時代,有幾位教授教課一塌糊塗,站在講台上,不是吹牛皮,就是出虛汗。這些課我都不願去,但有的老師特別在意出席人數,不去聽課,他就要記上一筆。不得不去上課時,我又開始心騖八極,神遊萬仞。人端坐教室一隅,呼吸停勻,眼睛也睜着,臉上可能還掛着一絲傻笑,思維卻在茫茫大荒中穿行。猛然驚覺的時候,恰逢下課。於是神與形合二為一,起身出門。真好。
神遊還是從人情應酬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的最佳方式之一。谷崎潤一郎在《客ぎらい》(厭客)中寫道,他成名之後,最怕找上門來閒聊的客人。每當與這種人相對而坐,聽他遊談無根時,谷崎就開始心不在焉,浮想聯翩,嘴上說着「對」、「嗯」,其實早將客人忘得一乾二淨,甚至想長出一條貓尾巴,輕輕甩一甩就可以表示「我在聽呢」,連開口應答都可以免了。
身體雖然無法自由,思想和情感卻不受禁錮,可以到處亂飄。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多形體與靈魂分離的故事。因為強烈的欲望和情感被壓抑或限制,雖然人還活着,魂魄卻離身體而去,做成了肉身無法做到的事情。唐傳奇《離魂記》說的是王宙與倩娘彼此愛慕多年,倩娘之父卻將她許配別人,王宙悲憤無奈,整裝遠行。倩娘思念心切,魂魄隨王宙遠走他鄉,身體卻留在家中,一病多年。後來這對戀人終於回鄉探親,倩娘病卧已久的身體出門迎接她的魂魄,二者合為一體。這個故事後來由鄭光祖演繹為元雜劇《倩女離魂》,在南宋姜夔的一首《踏莎行》中也有點化:「別後書辭,別時針線,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倉橋由美子的短篇小說《首の飛ぶ女》(飛頭女)化用中國和日本的古代傳說,講某女晚上頭部脫離身體,飛去情人身邊幽會,身體則留在家中,毫無意識地被養父奸污──倉橋由美子的寫作風格一貫如此,志怪奇譚中常有深刻的批判與反思。
在文學作品中,強烈的怨恨能在人還活着的時候產生「怨靈」,不受當事人意識的控制,去擊殺怨憎的對象。日本十一世紀成書的《源氏物語》中,主人公光源氏的眾多情人之一,是某位先皇的妃子六條夫人。她非常憎恨源氏的正妻葵,也怨源氏到處拈花惹草,卻無處發洩,暗中熬煎。在她不知不覺之時,魂靈兩次出竅,飛到葵和源氏的新情人夕顏身邊,將二人分別祟死。當六條夫人發現葵、夕顏二人的死因後,驚怖之餘,出家為尼。室町時代的能劇《葵の上》(葵上)詳寫了六條夫人壓抑、悲憤與矛盾的心理。舞台演出時,在全劇後半部分,原本戴「泥眼」面具(金泥塗眼之面,表現心懷怨恨的女人)的六條夫人換上猙獰可怖、頭上長角的「般若」面具,象徵女性在嫉妒與憤恨之下幽暗扭曲的潛意識。
六條夫人雖然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卻與她祟死的葵和夕顏同是男權社會的受害者。與六條夫人有關的古典能劇《葵上》、《野宮》等只是極盡描述她的悲哀與糾結,氣氛幽寂,文采華美。一九五四年,三島由紀夫改寫了《葵上》,作為他最滿意的一篇收入《近代能樂集》。六條夫人的化身六條康子,其怨靈具備了很強的主觀意識,有明確殺人動機。全劇突破了古代女性在兩性關係中完全被動的角色,引入現代男女之間微妙的情愫,在男主角與六條康子的怨靈和肉身同時對話中結束,而怨靈在瀕死的葵身邊遺留下的那副黑手套尤為引人遐思。
頭、魂魄和怨靈代表思想和主體意識,肉身則是盛放思想和意識的皮囊,要受風俗、地域、義理、人情和物理規則等等的束縛或壓制,不能隨心所欲,隨處亂跑。頭、魂靈在文學作品裏可以自由去來,算是一種消極反抗的方式,但在現實中,無論怎樣神遊都不可能對他人產生任何影響,只是一種自我消遣罷了。案牘勞形之時,百無聊賴之際,居家禁足之日,讓自己的靈魂逍遙,徘徊,彷徨,翩躚,恍惚窈冥,自色相的氤氳,升入形而上的遠域,「心目」(mind's eye)中翻騰起五顏六色,怪狀奇形:一隻穿花蛺蝶,一點燭光搖曳,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忽然,光怪陸離,雲散煙消,定定神,穩穩心,自己依然坐在書桌前,不禁自嘲:「又在發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