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溪林】DeepSeek和「未來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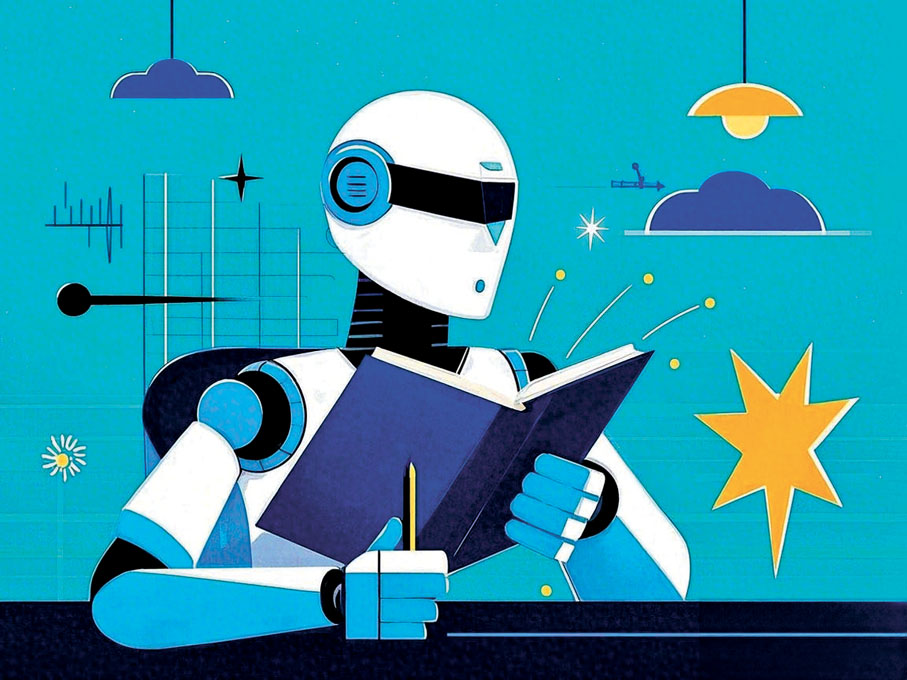
李 浩
新年以來,「人工智能」這個詞彙驟然升溫,火到出圈。春晚表演的機器人和DeepSeek一下子成為了無法迴避的公共話題,學生們談它,老師們談它,各行各業、男女老少都在談它……人工智能和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近,「人工智能改變生活」也越來越成為現實。作為一個寫作者,在這個時期裏我被追問最多的便是:「人工智能」能夠替代作家的寫作嗎?當DeepSeek不斷升級,兩年之後、十年之後,未來的作家應怎樣努力,他們應使用怎樣的手段才能保障自己不會被替代?
在談論向前的「未來」之前,我想先向後,看看過去的人們是怎樣面對這種可能產生替代的處境的。最具參考價值的可能是電影的出現,尤其是有聲電影出現之後。當時,也有一些人驚慌地認為「文學已死」至少是「小說已死」,因為小說中講故事的能力已經被電影強勢地「掠奪」和「擠壓」,電影中的故事既有直觀性又有更強的緊張感,同時它還讓故事變得更為簡潔、緊湊,無論是娛樂性還是感染力上都能不輸於小說,那,小說何為?小說還有它存在的獨特理由嗎?在經歷了不斷的嘗試和更變之後,小說還是活了下來,但電影出現之後的「小說」有了新的樣貌:譬如,景物描寫大幅減少,而它的描寫也多與小說中主人公的心境、情緒有關,和故事的隱喻性有關——電影能做得更好的,小說做出了讓度;再譬如,小說中的故事講述也由「描述一個故事」漸變為「思考一個故事」,更注意寓言性和象徵性,同時也有意地建立起多線的「復調」架構:這,是電影表達中較難達到的部分。我們還可注意到,小說的語言和小說中的感覺處理也有了諸多的變化,語言自身的藝術性和回味感是電影的表達手段不易處理的……還有一個支脈,在電影出現之後有一批「反故事」的小說出現,它們嘗試找出不同的、不會被替代的更多可能。
電影出現之後,小說(文學)必須要對這一新事物的出現做出回應,它一定要掂量哪些是它更適合的,哪些是電影這一新事物所適合的,它在做出必要讓度的同時也致力於重建和強化自己作為「獨立學科的獨特價值」,讓自己變得更不會被替代。是故,在DeepSeek出現之後,在它將以驚人的速度和「智力」不停不歇地突進之後,我們必須知道它可以「掠奪」「擠壓」和「取代」什麼關於這些,我們的文學可能需要做出部分「讓度」,然後,我們需更強化它不可「掠奪」「擠壓」和「取代」的方面——我們的「未來作家」應當緊緊握住這個不可替代性,同時巧妙而獨特地把必須讓度的部分做出新的「獨特」來。
在我看來,我們某些固定知識的文學將會被取代,至少是部分地取代。弱情感、弱文學性的平庸文學將會被取代。按照習慣的配方和基礎架構填充故事的那類小說將會被取代。個人標識匱乏的文學將會被取代。當然,那種反覆言說我們已經被社會學、哲學、心理學證實或證偽一千遍的道理的文學將會被取代,至少是部分地取代——它們原本也不太應是我們的文學褒有的,只是,DeepSeek會大大地加快這一淘汰進程,它可能會在不遠的未來就比一般的作家做得更好。
餘下的,能和DeepSeek抗衡、永遠不會喪失獨特性的部分,可能就是我們對於「未來作家」的期許,是「未來作家」們可依仗和應發揮的部分:
一、對人的存在的關注、對人類「沉默着的幽暗區域」的深度開掘依然是未來作家們重點着力的點——這類議題,DeepSeek可以輕易地從人類的已有經驗中完成歸納總結,但它應該不會有興趣替代人類思考,更不會有興趣帶着痛苦和自我審判的掙扎替代人類思考。這些屬於人類的事兒還得人類向「前所未有」進行推進,在這點上,卓越的作家將有他們永恒的不可替代性。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和複製第二部《狂人日記》或《阿Q正傳》,但魯迅獨有的思考和入骨的追問只有魯迅才能完成;
二、人類的真切情感和真正敏銳的感知,也是「未來作家」們不可替代的獨有領地,也始終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未來,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類並與人類一起完成諸多,但獨屬於人類、屬於碳基生命的那些情感是它永遠不會真切感受的,譬如瑪格麗特·莒哈絲《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中人物經歷的那些生活和它們所呈現的情緒情感。有時,它們可能並不具有完全的正確性,卻自有其認知價值。「美加憐憫——這是我們可以得到的最接近藝術本身的定義。何處有美,何處就有憐憫。」一位批評家曾這樣篤定地說道。這是作為硅基的人工智能難以達至的部分,當然它難以達至的還有慾望和貪婪,等等。
三、對於作家而言,童年經歷、時代精神、家庭環境和未知的X因素合力塑造着他們,也塑造着他們的獨特性。在DeepSeek越來越滲透到我們的文學生產時,作家的獨特性就變得更為重要,更值得強調。「未來作家」們大致會在為自己的作品打上清晰的個人標識方面更為用力,他們會讓自己的語言方式呈現更強的獨有性,會讓故事的結構和人物關係呈現更強的獨有性,會讓自己敏感和關注的人類議題呈現更強的獨有性——這越來越是對智力、思考、情感和語言感受力多重而綜合的考驗。
四、文學性,稀薄的文學性也是「未來作家」們必須要緊緊把握的,這既是我們為自己的作品打上個人標識的重要途徑,也是文學始終有魅力感和微妙感的根本所在。在談及《包法利夫人》時,納博科夫極有卓見地向我們指出:「在描述郝麥的粗鄙言行時,福樓拜運用了同樣的(指多聲部配合)藝術手法。內容也許粗俗低下,作者卻用悅耳又和諧的文字表現出來。這就是風格,這就是藝術。唯有這一點才是一本書真正的價值。」沈從文的《丈夫》,寫到了妓女和嫖客,但其中沒有一個髒詞兒,也沒有任何誨淫誨盜、引人聯想的文字,而始終保持着詩性的柔美和恰到的含蓄——我想,「未來作家」們或可從中獲得借鑒。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隨着DeepSeek和一切人工智能的發展,它對「未來作家」的幫助也會越來越大。它的發展會讓作家們巧妙書寫種種知識變得輕易,會讓小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百科全書」變得輕易,會讓寫作中「只能有讀者想不到,不能有作家想不到」的文學設計原則被作家們遵守變得輕易……真正有價值和意義的寫作,是不會被DeepSeek和一切人工智能替代的,對此我保持着謹慎但固執的樂觀。
(作者係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