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溪林】歷史為什麼對他選擇性遺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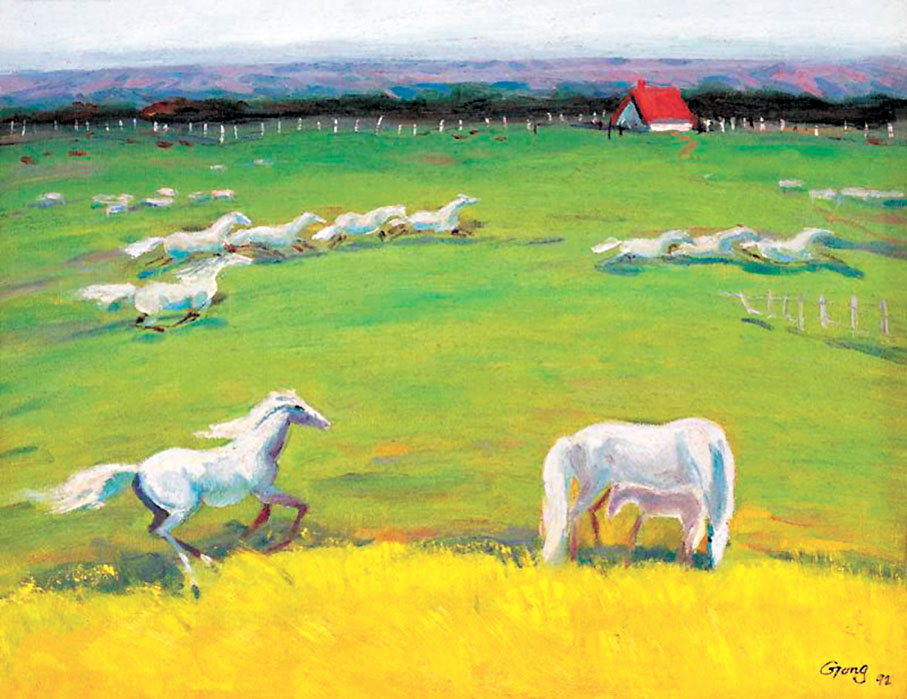
熊召政
在很長的一個歷史階段,對元朝及忽必烈的研究,一直諱莫如深。雖然我們從小就念過王朝更替的順口溜:「夏商周,秦漢晉,唐宋元明清。」而在史學界,口頭上雖然承認宋明之間有一個元朝,但研究元朝的史學家,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文學界更是這樣,無論是舊中國還是新中國,正面描寫元朝歷史的文學作品,一部都沒有。在較長一段時間裏,凡是涉及到元朝的文藝作品,其統治者基本上都被污名化或漫畫化,他們被稱之為「胡虜」,是入侵的異族。
這樣一種認知實在是由來已久。我六歲時,外祖父教我念舊體詩,讓我印象最深的有兩處,一是岳飛的《滿江紅》的那兩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二是陸游的《示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由此可見,在中國漢族的千千萬萬個家庭中,童年乃至少年所受的家教,就是要我們不忘國恥。國恥是什麼?就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圓、日寇入侵,宋明的亡國也被列為國恥。岳飛說「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講的是大金王朝入侵北宋都城汴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二人的故事。大漢天子陷入敵營中成了俘虜,這是何等難堪的事。滿人入關明朝滅亡,被迫出塞的江南詩人吳梅村,寫下的詩句同南宋的陸游一樣,也很沉痛,在《出塞》詩中,他寫道:
玉關秋盡雁連天,磧里明駝路幾千!
夜半李陵台上月,可能還似漢宮圓?
吳梅村大名吳偉業,是江蘇太倉人,與他齊名的還有一位抗清復明的鬥士、大詩人與學問家顧炎武,也經歷了王朝更迭之痛。他是江蘇昆山縣人,與吳梅村是鄰縣。兩人都是明末遺民,不肯仕於清朝,顧炎武學問比吳偉業大,但吳的詩名比他高。顧炎武也寫過一首亡國之痛的詩《古北口回首》之四:
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
卻恨不逢張少保,磧南猶築受降城。
無論是南宋的岳飛與陸游,還是晚明的吳偉業與顧炎武,都有着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在他們從小接受的文化教育中,君與國是連在一起的。國必定是漢人建立的王朝,君則是這個王朝的開創者與繼承者。如果不是這樣,士人乃至百姓就不會接受。為非漢人統治的王朝服務,就會被視為變節,成為「貳臣」,從而遭到口誅筆伐。
中原乃至江南的讀書人,從小就受到這種傳統的家國情懷的熏陶,沉浸既久,就形成了一種風氣:異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即是虜寇入侵,有氣節者,寧死不肯投降,文天祥、陸秀夫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便屈服於強權,內心也視他們為「沐猴而冠」,從而詆毀,不肯真心地合作。
客觀地說,我也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外祖父最早塑造了我的價值觀。我十六歲成為下鄉知識青年,在孤寂清冷的長夜中,讀到明末抗清英雄張煌言的一首詩《四辰八月辭故里》(其二):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記得第一次讀這首詩的時候,我熱血賁張很是激動,立即抄到本子永久保存。抄寫背誦這首詩,不再是外祖父的要求,而是我主動作為。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我的歷史觀已在家教中確立,我的家國情懷就是對虜寇的仇恨。
2005年,我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之後,我的這種狹隘的歷史觀才開始改變。
得獎的當年冬天,我被邀請前往參加哈爾濱市阿城區召開的金源文化研討會。我當時並不知道金源文化具體的指向是什麼,到了以後才知道,金源文化就是創立了大金王朝的女真人的文化。我在幾位當地的金源文化的研究者陪同下參觀了大金歷史博物館,也是第一次看到了這個被岳飛斥為「胡虜」的女真人的英雄群像。在這裏,大金王朝的創立者完顏阿骨打、吳乞買、完顏宗翰、完顏宗望等人物,都被當地人所尊崇,這是我在接受了「胡虜」這個教育之後,第一次看到了女真人的歷史以及他們如何入主中原的奮鬥歷程。應該說,這一次訪問給我打開了另一個理解中華民族的視角。過去,我都是聽漢人怎麼說,現在,我終於聽到了「胡虜」怎麼說。幾個月後,即第二年早春,我又受邀訪問了豫北平原的湯陰,並參觀了始建於明代的岳飛廟。岳飛是湯陰人,儘管周文王被拘的羑里城也在湯陰,但在老百姓的認知中,岳飛仍是湯陰城家喻戶曉的第一名人。他一直被尊為民族英雄,其岳飛廟更是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阿城與湯陰這兩次旅行,讓我看到了一個無法迴避卻又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即如何看待九百多年前的那一次宋金兩國的戰爭。湯陰尊奉並得到承認的岳飛與阿城尊奉的並建立了金國的完顏阿骨打,究竟誰是民族英雄,誰是中華歷史真正的推動者?
由此,我對這段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開始搜羅相關史料,通讀宋、遼、金三國史。2006年,我將研究史料的心得寫成一篇一萬多字的散文《夜裏挑燈看劍》,第一次提出宋、遼、金是中國中世紀的大三國。他們都為中華民族的拓展與傳承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文章寫出後寄給了北京的一家刊物,編輯回信說「內容太敏感」而婉拒發表。最終,這篇文章得到吉林《作家》主編的肯定給予刊登。爾後,《新華文摘》又全文轉載了這篇散文。我在文中主要的觀點是:大金伐宋造成的王朝鼎革,不是邊鄙的、落後的民族消滅了中原的、先進的漢人王朝,而是新鮮的、充滿活力的政治集團取代了腐朽的、沒落的統治集團。
我的這種歷史觀的改變是基於對史料研究的心得,以及對歷史趨勢的判斷。「漢」與「虜」在中華大地上實為一家,新中國成立時就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念,這個建國的綱領使華夷分裂變成中華一家。但是,傳統的思維習慣與漢人獨尊的文化觀念,並沒有在我們的認知中消除。相反,許多人(包括官員與一些學者)還秉持着舊有的思想觀念,發表一些不利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言論,甚至錯誤的決策。習近平總書記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這兩個字非常關鍵。只有在思想上、心靈上牢牢鑄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並落實到政策上行動上,這種符合歷史趨勢的更為寬闊的家國情懷,才能成為推動中華歷史前進的偉大動力。
基於這種認識,我在2019年完成了四卷本長篇歷史小說《大金王朝》,茲後,又投入到我的第二部長篇歷史小說《忽必烈》的創作中。(未完待續)(作者係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全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