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玉言/夏季的香港\小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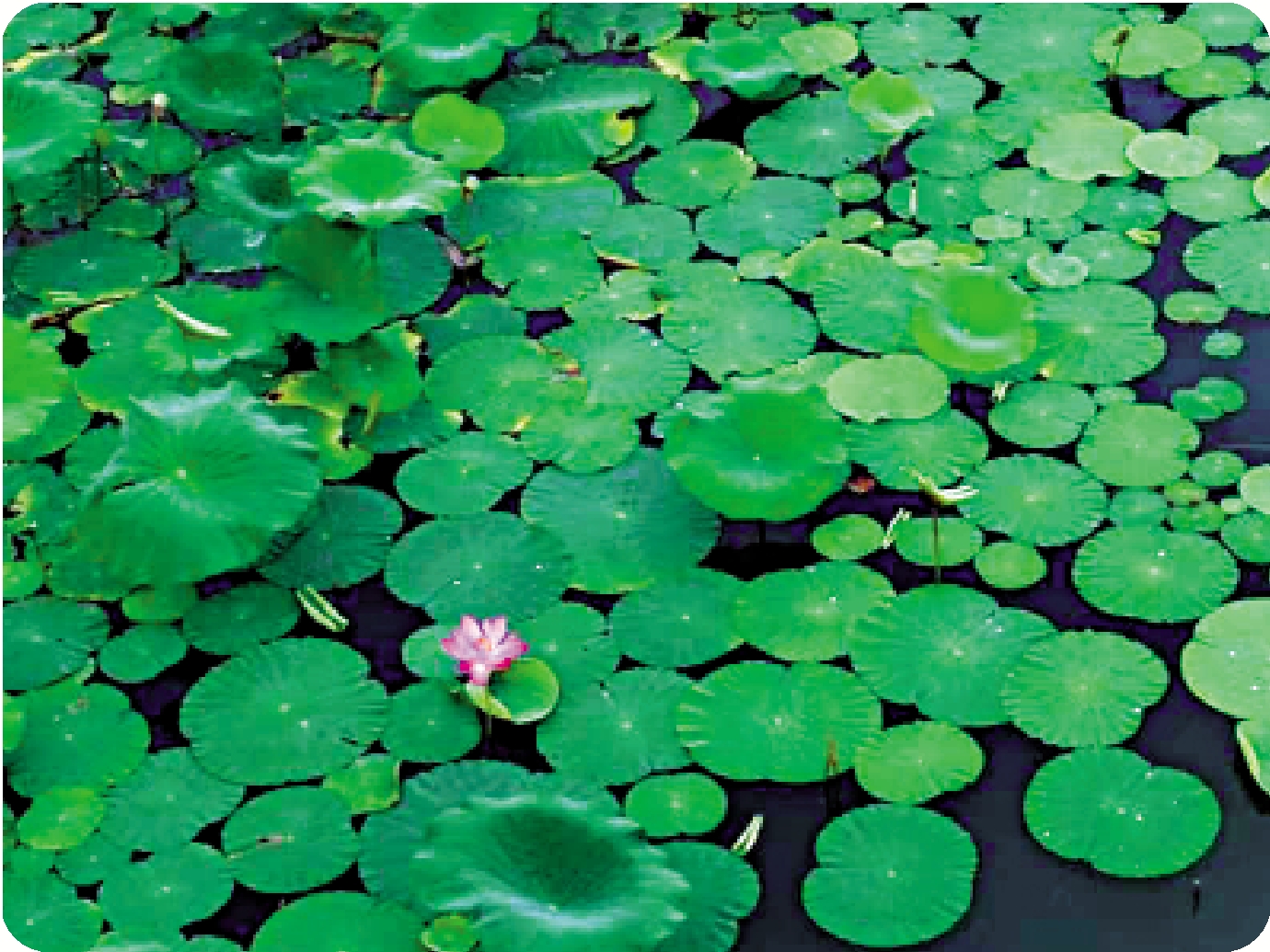
北京連續四十攝氏度高溫,「熱度」霸居全國之首。避暑勝地只有家裏。大街小巷可見的人影,多是為躲在家裏的人們送東西的快遞小哥。
閨密問我:香港比北京熱嗎?想想,似乎真不是。印象裏,香港的夏天很少超過三十四攝氏度,大多在二十七八至三十二三度之間徘徊。有時會悶熱幾天,空氣紋絲不動,小火煲湯似的熱法,那一定是悶着雨呢,不會持續很久。文火悶幾天後,一場豪雨傾盆而下,燠熱立馬消退。
這座有山有海的城市,也被山川海洋呵護着。山川海洋就是這座城市的天然大空調,靠近半山的堅道一帶綠植覆蓋的山透出隱隱幽涼,傍海步道海風拂面總是清涼。丘陵海洋造就了香港溫潤的氣候條件,熱冷都不極端。
哪怕走在德輔道或者皇后大道兩條橫貫鬧市的街道,無處不在的強大冷氣(香港空調機比較少冷暖雙功能,大多僅製冷,故港人慣稱空調為「冷氣」),會從大商場、寫字樓、餐館、港鐵口……但凡有門的地方滾滾而出。走熱了,隨便往哪個口一站,「寒流」一吹,熱氣減半。若想比較徹底降溫,進到商場酒店寫字樓大堂,不消一會兒立刻「速凍」。
也可以這樣說,但凡有門的地方,冷氣永遠保持在十八攝氏度。香港的冷氣,不僅用來控溫,也用來抽濕,否則人們會覺得透不過氣。所以一年四季、二十四小時不停。寫字樓內待一天,出到室外,再熱也不叫熱,是「暖和」。一天當中在室內吸收的「冷氣能量」,足夠支撐到家,一時半會兒不會化凍。乘坐巴士地鐵,想打瞌睡有點難,冷峻的氣溫讓你將「精神小夥」的氣質拿捏得死死的。在餐館吃一頓飯,也是一邊儲存熱量,一邊要用剛吃下的熱量「抗寒」。我的恩師當年參加談判在香港待了三年多,被「港式冷氣」吹得至今不敢開冷空調。
有港漂人自嘲「我是一隻來自北方的狼,在八月的香港凍成一條狗。」當你習慣了夏天在揹包裏塞一條披肩、小外套,這才算懂香港了。有的餐館會準備幾條厚披肩,如有需要可向服務生詢問借用。
此時,我在溫帶的北京艷陽裏揮汗如雨,亞熱帶香港的朋友可能在無處不在的冷氣下瑟瑟發抖。
夏季的香港,涼茶是祛濕解暑的恩物。街頭涼茶店擺滿成杯成瓶成桶各種顏色的涼茶,帶着不可名狀的草藥味的神秘氣息。
中環的百年老店春回堂,高峰時期平均日售上千杯涼茶。其所用中藥材達六百多種,包括許多稀有藥材,鎮店名物為龜苓膏、甜花茶和廿四味。鴻福堂是香港連鎖店最多的中式草本產品店,分店遍布多個港鐵站,他家的涼茶做成樽裝,夏枯草茶、雞骨草茶都有。
龜苓膏倒是在香港茶樓經常作為餐後甜品吃到。曾喝過一次廿四味,味道很中藥,似乎集合了所有的苦味……喝了胃痛、可能太過寒涼,弄得我有點怕了,其他味道的也不敢嘗試了。
香港之潮濕在乾爽的北京是難以想像的。空氣濕度通常在百分之七十左右,雨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牆壁地面都滲水珠。人們的常識是吃辣除濕,但港人對於辣味有着自己倔強的堅守,打風天超市各種蔬菜一搶而空,唯獨留下辣椒無人問津。疫情期間,公司飯堂區別南北菜的金標準就是一條:辣/非辣。
在港時,若想換換粵菜「口味疲勞」,就去有正宗湖南廚師的餐館,來一頓又辣又香、極其下飯的湘菜,既符合幹飯人要求,又解舌尖上的鄉愁。有時也去吃川渝味火鍋。無論哪家,堂中食客多為講普通話者。我的老領導曾長期在川渝地區工作,退休後夫婦倆自費來港旅遊,專門找了家川菜館約我見面。味道差強人意,倒是服務生小姑娘讓他們找到了鄉音。
內地大眾化的川菜,在香港檔次陡升。荷李活道那邊有一家隱在石階口的川菜館(好像叫「回憶」),魚香肉絲、宮保雞丁吃出了燭光晚宴的氣氛,食客多為老外。當然價格也不菲。居港幾年後發現,食辣水平不知不覺直線下降,對辣味的承受力跟香港本地號稱「能吃辣」的朋友差不多了。回京後,到湘菜館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港人外表似乎也「掛相」。網友總結出一些港人特徵,包括並不限於:現金支付、運動鞋、雙肩包、滴露搓手液、說話夾帶英文……一對照,發現自己幾乎個個「中招」,至今仍保留了「運動鞋+雙肩包」。港人即使西裝革履,也背雙肩包。個人體會:那是「真香」,舒服方便。還有加橘粉的甜豆花、餐後吃甜點或糖水、魚要清蒸才鮮……
居港「後遺症」種種,不知不覺。一一歷數,蠻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