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誰人不識君──詩人朔望一鱗半爪/成 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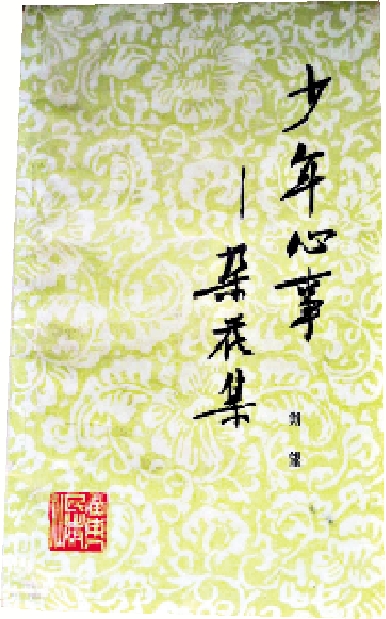
圖:《少年心事──朵花集》的封面
被譽為「江左才子」、活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壇的詩人、外交家、翻譯家畢朔望(一九一八至一九九九),現在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起來。而我雖然只跟他在杭州的一晤,卻至今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他是一座詩的大山,我在這裡寫的只能是一鱗半爪。
平生不會寫詩,卻喜歡讀詩、買詩集。粉碎「四人幫」後,迎來一個文藝的復興時代,詩歌創作甚為醒目。看到報上那些描繪劫後天安門「悲歡百代大廣場,風雨千般石未蒼」「一從好月重圓後,火樹冰輪盡華嚴」詩句,曉暢明快,朗朗上口,清新可讀,耐人尋味,感覺大有郁達夫的風格。原來,這些詩作是朔望所寫,也不知道他是何許人氏?
直到一九八五年,我到杭州初陽台創作園採訪,見到一位身材魁偉、濃眉大眼的長者,主從介紹這就是北京來的大幹部和詩人朔望,這真讓我喜出望外,讀了他的不少詩,今天才見到了真人。當時很鬧忙,也沒多交談,我只是表達對他的傾慕之情,而他卻答應回京後送我一本詩集。不久,真的收到了他寄來的詩集《少年心事—朵花集》,不但寄來了書,還在書的扉頁寫了一段長長的題識:「此為年前舊作,殊無足觀。要之亦只留一點歷史殘味,手頭無書,只得以殘物摭拾充數,聊表寸意而已。俟日後新集問世,再補此衍,乞諒。朔望八五年三月中旬於北京。」雖只一百二十多頁一本薄薄的書,我卻如獲至寶,深藏三十多年完好如初。遺憾的是,他答應「新集問世」,成了絕響。
朔望到杭州參加創作活動,跟他對杭州的特殊情感有關。他原名「慶杭」,一九一八年出生於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童年是在杭州湧金門外「柳浪聞鶯」度過的。他聽慣了湖邊村姑們啪啪劈劈的搗衣聲,暮春三月柳蔭梢頭新燕的呢喃,夕照山麓渾如老衲的雷峰塔影。他曾寫詩道:「鶯柳不關詩歲月,皆因西子最宜家。」「吾生猶得見雷峰,劫罷熏陽分外紅。」六歲那年,他隨父親來到繁華的十里洋場大上海。九歲時父親撒手西去後,他一度寄養在父親的好友、著名通俗小說家包天笑家中。他父親筆名畢倚虹,也是清末「禮拜六派」主要代表作家之一。
由於對朔望的仰慕,他發表在報紙上的詩不忘漏過。為了懷念朔望,我翻尋舊筐,竟藏有七篇之多,大都發表於人民日報(包括海外版)、光明日報和新民晚報等,以格律詩居多,也有新詩如《風雪鈴語》。剪報已經發黃,但字跡清楚。其中有一篇一九八八年四月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贈台海王拓》,包括他自己在內共十一人的詩,有邵燕祥、常任俠、冒舒湮、王辛笛、李汝倫等名家,而且寫了一個長長的題識,大意是晤台灣作家王拓,「我久慕王君,是夕雖只隔座遙呼,亦殊快慰。歸誦邵作,呵凍步韻一首,未計工拙。」「臨行,邵燕祥囑以一卷交王」「天下秀才人情,無非伺機相濡以沫耳。」
這位以「江左才子」著稱的詩人,說他渾身是詩也不過分。一九七九年秋,時任中國作協外事辦公室主任的畢朔望陪外國友人赴杭州參觀訪問。在奔馳的火車上,他讀到張志新事跡,掩面大慟而泣,嗚咽有聲。入夜輾轉反側,幾不能寐,以憤怒的筆觸,寫下了那首京華為之轟動、名噪一時的《只因……》。
只因你犧牲於日出之際,監斬官佩戴的勳章上顯出了斑斑血跡。只因你胸前那朵血色的紙花,幾千年御賜的紅珊瑚頂子登時變得像壞豬肚一般可鄙可笑。只因夜鶯的珠喉戛然斷了,她的同伴再也不忍在白晝做清閒的饒舌。只因你的一曲《誰之罪》,使一切有良知的詩人夜半重新審視自己的集子。只因你恬靜的夜讀圖,孩子們認識了勇氣的來歷。只因你的大苦大難,中華民族其將大徹大悟?
一九九六年,朔望的一批同學應滬上同學之邀,從昆明、西寧、長春和台灣等地到上海聚會,他因事未能赴會,即致電祝賀,也寫了一首詩:「夢覺天涯,須忍淚,莫問紅塵何世?宴開梅隴,且借興,共慶白首群星。」朔望以詩聞名和傳世,兼及翻譯、新聞、外交等諸多領域,著作頗豐,一九三○年即發表作品,但至今未見有完整出版展現。查閱有關網頁,也只有三十多年前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年心事—朵花集》一冊,似形單影隻,孤獨無依,但願這是我的孤陋寡聞吧!朔望的遺作,不僅是一位著名作家、詩人創作的豐碩成果,也是我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能不引起有識之士、他的親朋友好和出版界的關注嗎?我國是一個詩的大國,沒有理由對這個詩的兒子太冷漠了吧!他的詩作遍布神州大地,留跡世界,他從重慶寫到北京,從新德里移往巴黎,四海誰人不識君!
西湖碧波泛舟,漣漪清清,時時會撥動?她的兒女掛牽。終於有一天,西湖游子歸來了!二○一○年,我接獲年過九旬的老前輩楊覺農贈我一冊自傳體的《衰翁絮語》,讀?讀?,竟發現朔望是他在中央政大的同學,書中有多處提到他的蹤影。一九三九年發生芷江學潮後,學校開除了一批學生,朔望便去了新華日報工作。他在書中寫道:學校開除的一批同學中「也有共產黨或傾向共產黨的同學,如早期的范長江和九期的畢朔望。朔望如與共產黨沒有聯繫,怎麼能一下進入新華日報社工作」。楊在那個極「左」年代,冤屈纏繞,身陷囹圄,歷經坎坷,才得平反。一九八三年,闊別數十年後的朔望夫婦,到杭州蕭山探望他的同窗老友。這次重逢,得益於鄉賢詩人、作家邵燕祥的聯絡。後來畢數次到杭小住,均約他去暢談。書中還附有一張寫有朔望題識的他倆合影,朔望也為他拍攝了一張凝視西湖的單影,象徵?他的坎坷人生。
聞悉這些信息後,我致信楊老探詢朔望的近況。蒙他覆信詳談,他在信中說:「想起朔望,他晚景亦悲涼。過八十後,患冠心病綜合症,一個大胖子竟然骨瘦如柴。自陶××(妻子)姐患CA去世後,與後期校友黃×結婚。朔望病後,她竟然回南京老家,後又去美照顧孩子。朔望一家六口被安排到五個地方勞動,無一人有出色成就,全仗一個保姆,一個敬慕他的女文友照顧。朔望,人稱「江左才子」,中英文俱佳,家中藏書甚豐,多為外文,後繼無人。其同胞長兄畢季龍從聯合國副秘書長任上退休,數年前尚在上海,近況不明。」楊老給我的這封信寫於二○一○年十月四日,其實,朔望已於一九九九年在北京逝世,嗚呼,一代才子,悄然離世;一顆詩壇之星,就此隕落!媒體也無信息,更不見紀念之類活動,以致不少文壇他的友好還在打聽他的情況哩!誠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不久,他的同窗摯友楊覺農也追隨而去,享年九十四歲。他們到「天堂」相聚,切磋同窗之誼,追索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足跡。
